王大高·我听父亲讲抗战

二0一六年十二月一日(农历十一月初三)凌晨三时许,我的父亲王昆岭于永济市蒲州镇花园村家宅寿归正寝,与世长辞。在遗体告别仪式上,来自北京、西安、太原等地的有关领导、朋友和花园村村民为他送行。山西省黄埔同学会秘书长路支前同志宣读了徐向前元帅长子、解放军某部中将徐小岩同志从北京发来的唁电。唁电中写道:“王昆岭同志为抗战胜利和民族解放做出了卓越贡献,并竭其一生为国家建设事业奋斗不息,堪称后人楷模。王昆岭同志身上体现出‘爱国、革命’的黄埔精神和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远大理想将永远激励着我们不断前行,不断推动祖国和平统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军礼深情
二0一五年九月三日,他佩戴着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为他颁发的抗战胜利七十周年纪念章,穿着整齐,早早坐在床边等着观看阅兵式实况转播。当画面上出现宏伟壮观的阅兵场面时,他热泪盈眶,面色凝重,默默地举起右手行起军礼,久久不肯放下。这个军礼在九月四日中央电视台晚间新闻中作为特写镜头向全国播放。这是我的父亲生前的最后一个军礼。在此之前,山西省有关部门曾推荐他去北京作为抗战老兵代表出席阅兵式和山西省在武乡举行的相关活动,因身体原因,他未能成行。
二〇一五年九月,山西省在太原市南文化宫举办了《民族脊梁》山西抗战老兵摄影展览。父亲作为山西省在世的黄埔学生中职务最高的抗战老兵,照片悬挂在显著位置。展览期间,时有抗战老兵和现役军人在像前行军礼,表示敬意。多名摄影家用镜头记录下了当时的情景。
父亲过去很少向我们提及他在抗战期间的经历,尤其是在政治动乱的年代,他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更是缄口不语。直到改革开放后他得到平反,认定了他的起义功绩,特别是在二00五、二0一五年他两次获得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的抗战胜利纪念章后,他才打开了话匣子,讲了很多当时的场景和他的亲身经历。令人惊奇的是,他虽然年事已高,对眼前的事常有遗忘,但对那个年代的人和事,讲起来姓名籍贯,音容相貌,来龙去脉,娓娓道来,如数家珍。讲到激昂时,站起来挥舞拳头;讲到悲愤时,几度哽咽,他讲得更多的是当时的战事和他的战友,很少讲到他自己。只是当我们问及时,才讲出一些。我只能根据当时的记录和他生前写的自传整理出来,作为对父亲的怀念和敬意。
千里投军
蒲州王家曾是名门望族。先祖王凤三是前清举人,在京城为官。因在家休养期间为黄河沿岸灾民减赋与当地官府抗争而受到民众拥戴,在花园村为其立碑纪念,人称“王举人碑”。后因社会动乱,家境衰落。父亲兄弟五人,排行老四,幼时聪颖好学。因家中人多地少,经表兄任万青介绍,只身渡过黄河到陕西省平民县(现为大荔县)第一高小半工半读,敲钟打杂,供自己上学,时年13岁。一九三七年,卢沟桥事件爆发,国人群情激愤,全国各地纷纷成立抗日组织。平民县也成立了抗敌后援会,18岁的父亲担任了宣传干事。一九三八年,时任国民党五十二军军长关麟征秘书的平民县人氏王伯珍参加台儿庄战役胜利后回家探亲。当地召开欢迎会并请他演讲。父亲亲自参与了发动和组织。在演讲会上,王伯珍讲了日军的暴行,讲了抗日战场的惨烈,还讲了关麟征将军决心以身报国、誓死抗日的英雄情怀。父亲听了十分感动,热血澎湃,立即找到王伯珍要求投军参战。蒙允后与王伯珍的兄长一起先到河南,得知五十二军经徐州会战后已划归第六战区,开赴江西瑞昌作战。父亲赶到汉口遇见由前线来往运送伤兵的汽车,才随车来到江西阳新找到部队。当时五十二军长关麟征由于台儿庄会战有功,升为三十二军团长正指挥三个军在九江和武汉之间与日军激战。父亲由秘书引见关司令面谈后,关司令说:“这小老乡,又没打过仗,就留在司令部吧!”随即手令父亲任军团司令部参谋处准尉司书,负责文书信件整理。因参加军训刻苦,工作认真负责,性情耿直,为人忠诚,又写一手好字,很得关将军赏识。不久,又调任关将军上尉待从副官,执行追随关将军外出开会和检阅部队外勤任务。之后又保送到贵州遵义参加译电员培训,三个月后,回来成为关将军机要秘书。之后又担任了司令部少校参谋。先后随关将军参加了武汉会战、湘北会战、长沙会战、文山保卫战、远征军第一方面军赴越南对日作战等战役。
武汉会战
父亲参军后,立即随关麟征将军投入了对日作战。当时关麟征将军正指挥三个军与由九江向武汉进攻的日军展开激战。当时我方在瑞昌、阳新之间,利用有利地形阻击日军,日军第九、二十七两个师团日夜轮流猛攻,均被击溃,部队坚守四十多天,敌人始终未能前进。但我五十二军伤亡极为惨重,奉命撤至湖南补充整训,其余部队由第五战区汤恩伯集团接防。后我部又在金牛镇构筑预备阵地,与日军激战十余日,掩护汉口军政和民众安全撤退完毕,汉口失守,武汉会战结束。父亲在回顾这一段经历时说:“我当时不到十九岁,虽然没有直接上前线,但作为司书要记录下关将军指挥大战的全部过程,也切身感受到中日大战的残酷。可以说,我开始认识到什么是战争,什么叫你死我活。说实话,刚开始也有些害怕,但随着战争气氛的感染,恐惧之心全无,只想着怎么抗击日寇,收复失地。而关将军那种临危不惧,有勇有谋的大将风度和魁梧的形象、渊博的学识、豪爽的性格使我十分钦佩,加之他对我的信任和关怀,使我下了决心追随他报效祖国。他在抗战后期担任了陆军总司令,又任黄埔军校校长,因与蒋介石不和,未去台湾,选在香港定居。病逝香港后又移葬英国旧金山华人永久墓地。”
参战长沙
父亲直接上前线作战的战役是第一次长沙会战。一九三九年九月十四日开始的长沙会战,是二战在欧洲爆发后,日军对中国正面战场采取的第一次大规模攻势作战。当时任五十二军军长的关麟征已升为第十五集团军总司令,划归薛岳任司令长官的第九战区,开赴湘北参战。第五十二军作为主力军驻守新墙河一带阵地,与驻守长安桥一带的七十九军、驻守湘阴一带的三十七军共同负责对岳阳方面侵华日军的防御。
秋日的湘江上战云密布,一场大战临近了。九月中旬,日军抽调第六、三十二、一○六师团主力等共约10多万人,在冈村宁次指挥下,从赣北、鄂南、湘北三个方向向长沙发起进攻。
在湘北方面集结岳阳地区的日军第六师团与奈良支队,约5万余人,从9月18日向新墙河北岸守军阵地发起猛攻,我五十二军奋力抗击。23日,日军在炮兵、航空兵协同下,八次强渡新墙河未果后,施放毒气瓦斯,再次强渡新墙河。五十二军损伤残重。25日,五十二军奉命向汩罗江南岸转移。27日,第九战区按照在长沙地区与日军决战的计划调整部署,调集6个师的兵力在福临铺设伏,日军遭重创。29日,日军第六师团一部在石门痕遭到伏击。30日,我军又向驻守永安、上杉、石门痕的日军发起猛烈反攻。10月1日,日军开始撤退,我军连续追击,收复了汩罗、新市等处。14日,双方回复战前状态。第一次长沙会战宣告结束,时人称之为“湘南北大捷”。
此次战役中,日军集中了10万兵力,伤亡达两万人,并未达到歼灭第九战区第十五集团军的目的,反而遭到有力阻击、侧击,损失残重,匆匆撤退,士气大挫。
从战前布防,构筑工事,演练,到战后休整总结,父亲追随关将军参与了长沙会战全过程,经受了战火考验。父亲回忆说,历时四十多天,他和关将军没睡过一个安稳觉,没吃过一顿安稳饭,阵前战士互相用刺刀理发,机关枪管打红了就尿泡尿降温,战士负重伤疼痛难忍,就向自己开枪。许多场景和对日军的深仇大恨他永生难忘。期间,五十二军防线曾被日军击破,我军一部被日军包围,通讯中断,失去联系。第十五集团军司令关将军十分着急。父亲受命带领一支小分队穿过日军防线,找到我方驻军。战斗十分激烈,阵地几次失而复得,我军伤亡过半,急需增援。父亲只身再回闯日军防线,步行一天一夜,深夜时,返回我方防区。因实在走不动了,就摸进一座庙宇内,推开土炕上睡着的一排国军说,“挤一挤让我也睡一会儿”。天快亮时,父亲被冻醒,一看炕上炕下都是国军士兵的死尸。父亲起身返回司令部,向关将军汇报前方战况,后派兵迂迴增援,接应前方部队突围。父亲多次说,“我是真的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
入滇御敌
一九四〇年,关麟征率五十四军开往广西柳州划归第四战区归张发奎指挥。当时,日军已占领越南,除切断我方由越南方向的国际补给线外,还企图由越南向云南进攻。父亲所在部队组建远征军第一方面军奉命经柳州,桂林、昆仑关,由小路日夜兼程,长途行军,由广西开赴云南滇越铁路以南八寨、马关、麻栗坡一带,开始构筑永久性国防工事,有效地抵御了北犯日军。司令部驻扎云南文山。父亲说:当时发生了两件事儿。一件是当他们长途跋涉,刚到昆明,被当地政府安排住宿。第二天,日军飞机对昆明进行轮番空炸,有一颗炮弹恰巧落在父亲所住的床上,但幸好没有炸,父亲幸免一难。当地政府还根据所受损失赔了父亲60块钱。第二件是,一位蒙古商人敬佩关将军的抗日功绩,赠送了两匹蒙古战马,威武雄壮。父亲曾指着关将军骑马照片对我说,另一匹由关将军指定由我乘骑,两匹马都由我管。关将军对这两匹马非常喜爱,每匹马每天还要喝一桶茶。
一块银元
在文山驻扎后期的一天,由第九集团军特务营副营长护送来一位在越南向中方投降的日军少校到司令部。关将军指令交由父亲接受并与父亲同住一屋。当时日语翻译十分缺乏,也急需了解日军机密。这位反战少校帮助我方做了很多工作,也与父亲同吃同住,关系十分友好。他教父亲学日语,父亲教他学汉语,关将军还请他们俩吃过一顿饭。一个多月后,美军得知这位少校曾在南海一座小岛上服役。而这座小岛上有日军一个很大的军火库,因地形复杂,十分隐秘,美军飞机几次轰炸都未见成效,便向我方提出要把这位少校移交美军。临别前,父亲与这位少校依依不舍,互赠礼物。这位少校拿出自己仅有的一块日本银元送给了父亲。之后他们失去了任何联系。文化大革命期间,抄家之风盛行,父亲忍痛将在军队时期的衣物和照片除一只皮箱和一个公文包外全部销毁,而这块银元始终被父亲所珍藏。八十年代,一位日本的访华记者得知此事,要用一部日本相机换这块银元,被父亲婉拒。父亲说,这块银元使我认识到,日本不仅有侵略者,也有反侵略者,也有帮助中国抗日的好人。两国人民都希望和平。 黄埔铸魂
父亲在五十年代所写的自传中讲道:“我参加部队以后,时刻感到自己文化素质差,军事知识薄弱,不是一个合格的军人。故加紧自学中学主要课程,准备上军校。一九四二年,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即黄埔军校)招考第十九期学生,我向关将军恳求,承蒙允诺,报考并被录取。”此时,关将军又出面保送父亲到黄埔军校五分校(设在昆明)军官训练班第十二期学习。因学员都是大部队保送来的军官,故免去了半年的入伍军训,直接进行了地形学、通讯学、攻防战、野外勤务、多兵种指挥学、班排连团训练科目等军队指挥员的严格训练。军官训练班在黄埔军校历史上只办过这一期,教官除了中方教官外,还有不少美籍教官。在校期间,父亲还参与了由教官李希杰主持的《测图实施计划草案》一书的编写工作,并担任第二十七小组副测手。父亲的同期同学中,既有国民党员,也有共产党员,学员的抗日热情十分高涨,彼此结下了深厚友谊。父亲坚定的反对内战、一致抗日的思想就是在这里形成的。二OO九年,我在中央统战部组织的学习考察团在云南昆明活动时,来到曾是黄埔军校五分校的“讲武堂”参观。在现场我与父亲通了电话。父亲用充满兴奋的语调告诉我,进了大门对面高台上是长官训话的地方,左手一排小楼是教室,他在第一个教室的第二个窗户下就座,右手一排小楼是宿舍。学校后边是武器库和学员吃饭、洗澡的地方。学校对面是翠湖,是学员课余时间散步的地方。沿惠通路向西,惠通寺是当时集团军司令部的驻扎地,不远处的惠通旅社当年是关麟征的住宅。学校毕业后,他仍回到原部队,后又到二十五师任少校参谋。战友情谊
父亲在晚年时,十分怀念曾经在抗日战场上生死与共的战友。经常说起,有些战士牺牲时连姓名、籍贯都不知道。因父亲当时从军时是从陕西去的,改革开放后,在香港、台湾的原黄埔同学曾多次到陕西找他。后来知道他是山西永济人,便直接找到父亲当时所在单位普救寺管理处。得知家境并不宽松时,还多次予以资助。和父亲交往时间最长,关系最为密切的是关麟征将军的女婿,在香港政府消防局供职的柯大澍先生。他们互相通信十多年,从未间断,直至柯先生逝世。二〇〇五年,我率绛州鼓乐团赴新加坡演出,途径香港时,受父亲之托,到香港九龙新围街柯先生家中拜访了柯先生。柯先生及夫人非常激动,热情招待,并为父亲捎了不少东西。柯先生满怀深情地给我说,你父亲救过我两次。一次是柯先生因工作失误,关将军要重罚。我父亲说情,免了重罚,调出司令部下部队当了团长。另一次是他在部队得了病,住了医院,急需一种特效药,但没有钱不能从外国人开的医院买到。恰在这时,父亲请假到城外看他,得知情况后,赶到医院,拿出自己刚发的全部薪水和临走时关将军让从账房拿的一些钱,买到了药,才治好他的病。在当时,那可是一笔不少的钱。我回来后,对父亲讲了这些事。父亲说,第一件事,他记得清楚。第二件事,他早忘了,但这次一说他又想起来了。
柯先生在一封写给父亲的信中开玩笑地说:“你还记得在行军中你因病坐担架,病好了也不下担架的事吗?”我在翻阅整理信件时,看到了这句话,问了父亲是怎么回事。父亲大笑说:“我当时确实有病,但身为机要秘书,又随身携带着重要文件,必须紧随关将军一起行军,便由当地政府派民工抬担架,抬我行军。中途我感到好一些了,要求下来步行。但民工死活不让我下担架,他们说你不坐担架,让我们长官知道了,不但要扣掉我们的所有工钱,还要重罚我们。这时我也让柯大澍上来坐,他也不敢,因无病坐担架也要受到军法处置的。这事他清清楚楚,却老了老了还开我的玩笑。”父亲还说,那时他们都才二十出头,又都单身,朝夕相处,亲如兄弟。大澍他一米八几,篮球打得好。有次因打篮球误了开会,差一点被关禁闭。还是父亲给他打了圆场。父亲当时佩戴的是一把德国造手枪,他想要,父亲报告关将军也给他配了一把。
河内受降
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父亲所在的二十五师奉命由马关、麻栗坡进入越南,接受日军投降。父亲被任命为先遣参谋,以中方联络员身份率领一个营兵力,向河内进发,负责与日军接洽安排受降事宜。途中遇到法国军队阻击。他们认为越南曾是法租地,应由他们接受日军投降。父亲当即立断坚决还击,交战了一个多小时,通过喊话,法军举白旗投降,部队顺利到达河内。父亲作为中方联络官对日军联络官的无理要求和傲慢态度义正言辞,进行了坚决回击,捍卫了中国作为战胜国的尊严,迫使日方按中方要求在美国军舰上签订了交接协约,等待龙云等将领来越南正式举行受降仪式。率部义归
还未等到受降仪式正式举行,父亲所在部队又奉命乘坐美国军舰在海上历时七天七夜,赶到东北,经山海关、锦州,在葫芦岛接受日军投降后,进入沈阳与苏联军队共同接受日军投降。此时,因长期战乱,市区内土匪众多,社会治安十分混乱。经中苏双方洽谈,成立了中苏军警联合稽察处,各出一支部队维护社会治安。父亲担任中方代表兼办公室主任。经过紧张工作,抓捕市区内的各种土匪势力和日军残余势力,社会秩序有所好转。一九四六年,父亲奉命回原部队,担任二十五师辎重团团长。此时,内战爆发,部队内部的反内战情绪很大。父亲与解放军某部苏部长取得联系,引势利导逐步做好了起义准备,约好先按兵不动,以防不测,待条件成熟后阵前起义。不料父亲突然听到消息,要调他进城任师代参谋长。父亲十分焦急,唯恐部队失控,起义落空。在与苏部长联系后,托辞未去就职,于一九四八年将整团兵力配合曾泽生率部起义时,全部移交中国人民解放军。因父亲离家十多年时间,我的奶奶在老家因思念儿子哭瞎了双眼。父亲思乡心切,谢绝了解放军的挽留,于50年带着妻儿和自己的部分财产回到了山西永济老家,与家人团聚。至此,结束了他的军旅生涯。
父亲在回忆他的抗战经历时,反复说,往事不堪回首,但又很难忘怀。我们饱受战争之苦,也深知和平来之不易。作为一个中国人,必须爱国。当祖国有难时,不能各顾各,一盘散沙,都要挺身而出,精诚团结,为国效力。因为只有国家独立,稳定,我们的日子才能过得好。今天我们生活幸福了,不要忘记那些为国捐躯的先烈,没有他们的殊死斗争,我们就会当亡国奴。今天我们无论遇到多大困难,甚至受多大委屈,但一想到他们,我们还有什么可怨言的。共产党英明伟大,让中国繁荣昌盛,人民过上了好日子,外国人也不敢小看中国。父亲非常关注全国和山西省黄埔同学会的活动情况,他的床前摆放的全是《黄埔》杂志,每期必看,有些文章还反复阅读,而且多有感慨。父亲还十分关心台湾问题,每天要看中央电视台的“海峡两岸”。他说,国家一定要统一,一定会统一,搞台独,不得人心,没有好下场。我多么希望在有生之年能看到台湾和平统一啊!

相关文章

最新推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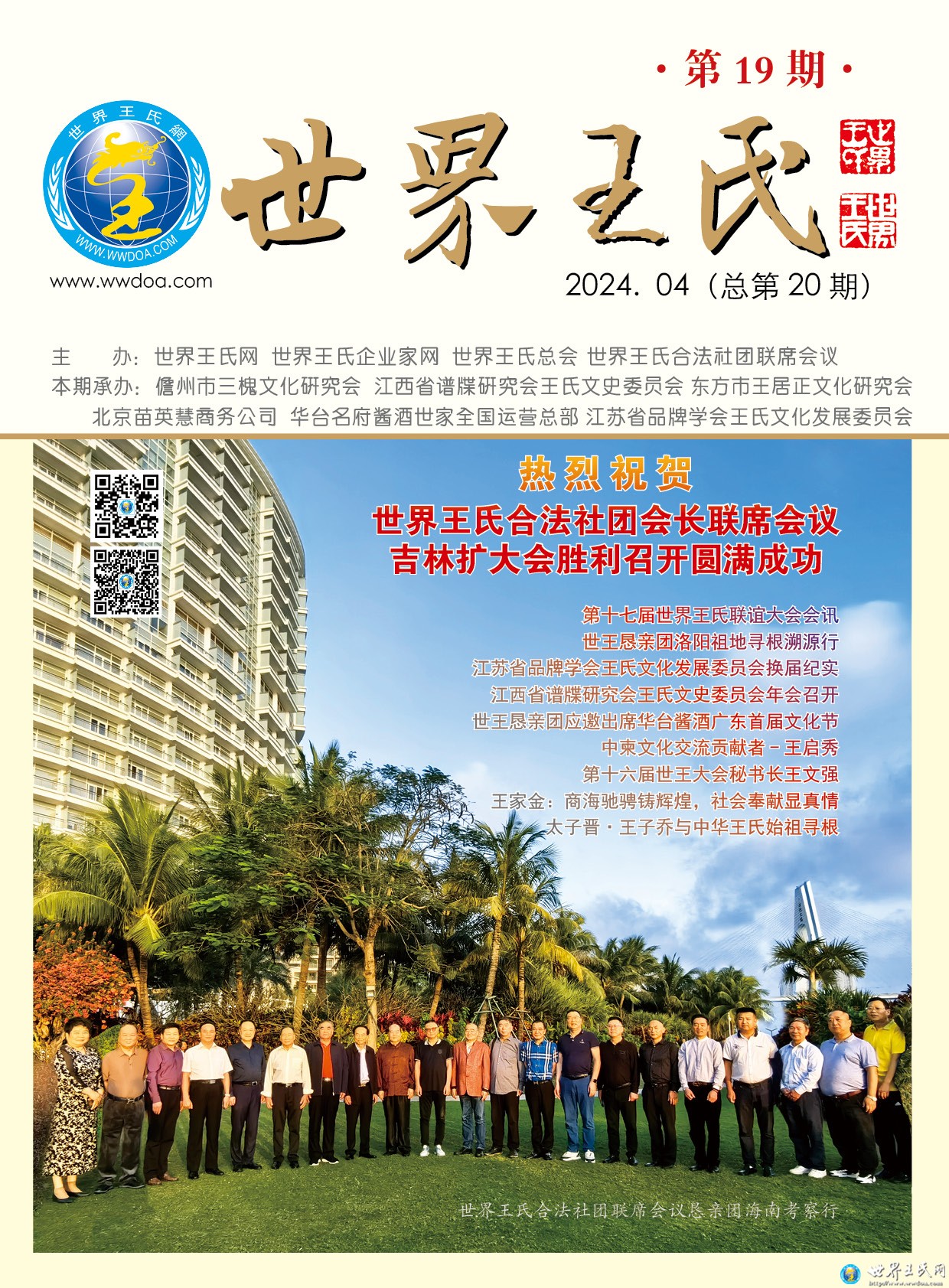
《世界王氏》第19期总
《世界王氏》第19期总第20期(电子专刊) [详细内容]
- · 王大高·我听父亲讲抗战
- · 《世界王氏》第19期总第20期(电子专刊)
- · 《世界王氏》第20期总第21期(电子专刊)
- · 新质领航 再创辉煌——张家口浙江商会
- · 河北执行会长王清海·世联会议赠语
- · 《世界王氏》第21期总第22期(电子专刊)
- · 《世界王氏》第18期总第19期(电子专刊)
- · 广西会长王梅林·世联会议发言集萃
- · 福建漳州王开忠·世联会议发言集萃
- · 王维华——族歌嘹亮响九州
最新排行
- · 王岐山罕见照:与习近平刘源聚会曝光 (1)
- · 王友明:风霜雪雨数十载 笔耕不辍写人生
- · 王琼与晋祠
- · 山西王家一门三进士
- · 隋朝大儒王通三子·人品高洁王福畤
- · 王小波的父亲王方名
- · 大唐名将太原王忠嗣
- · 定远将军王孝礼
- · 战国末期秦国宿将王龁
- · 王慧龙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