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开封三槐堂王氏历史文化研究会期刊 总第一期(2)
关于抢救和开发三槐堂的请求
开封曹门关中街的三教堂是前身,是北宋著名的太平宰相王旦(字子明,又字延龄)的家词,即三槐堂。“三槐世德,两晋家声”,响誉历史,而今很多名人都出自三槐堂王氏,这是开封市的骄傲。并且多少年来,久唱不衰的包公戏,王延龄也成为清官和智慧的化身。而今开封包杨两府再现辉煌,唯有开封三槐堂遗迹荡漾无存,现仅存的三间三教堂遗迹频临拆迁的威胁。
因此,为了开发弘扬三槐堂历史文化精神,继承和宣传王旦当国唱大雅,宰相肚里撑舟船,治理国家,发展经济的治国文化精髓和良好的家风,吸引海内外几千万三槐堂王氏后裔寻根问祖,投资建设,振兴中原经济,呼吁开封市委市政府及有关部门高度重视抢救和开发三槐堂工作,抢救历史文化,保护历史古迹。同时,呼吁海内外三槐堂王氏后裔共同努力,通过各种渠道保护和开发我们的家园,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再显三槐堂的辉煌。
中国开封三槐堂历史文化研究会
2012年3月15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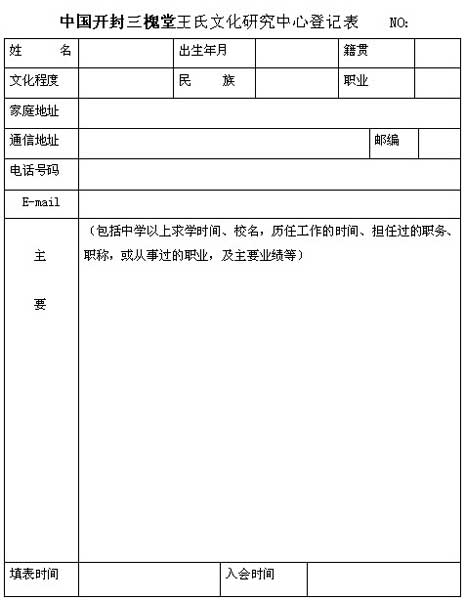



王祜与王佑不是同一个人
三槐堂始祖王言,在唐末曾多处为官,其中还在江西玉山县任过邑令,对此诸多王氏家谱有记载,无独有偶,他的孙子王祜,也曾在玉山县当县令,后来升迁为江西按察史,累至何职,终无祥考。 二00四年春节初二,我全家到三清山旅游,在旅游图上,发现有一个名叫王祜的宋代墓景点,怀有好奇之心上去一观,王祜墓处于龙虎岭上,旁边有一座风雷塔,是王祜过世后由皇帝封赠的伴葬物。当时,我也不知王祜是何许人,我还没有参加中华王氏研究会,对王氏历史上的许多问题知之甚少,在参加研究会后,我认识了很多末知的问题,特别通过三年的研究,确定王祜和王佑不是同一个人,理由有三,一、王祜和王佑在宋史和家谱中常以不同名出现,在永泰王氏家谱和其他王氏家谱中说明王言之子王彻有三子,一为王祜,二为王佑,三为王祉,而王祉的后代大都在浙江。现在要弄清为什么总是把王祜和王佑的事情混淆在一起,首先要弄清三清山上王祜的经历。纯清后,可以拨正各派的世系缘源。二是王佑的墓葬在陕西,而王祜的墓在江西,是不同的西,一个在江南,一个在黄河以北,相去甚远。三是迁来江南的谱谍中都是记载王佑为先祖,末曾看到王祜的名字,王祜究意何时来江南,还是个悬案,要解除种种疑团,我研究会须派员亲临玉山县上的龙虎岭一观究竟,有难解之处,可翻阅上饶史志和玉山县地方志来寻找答案,这个问题必须要弄清,否则对后来的工作为产生不真实情况,历史的经过,要以真实为前提,如查清这一事实还会有更意外的收获,为进一步弄清三槐王氏源头和派脉关系奠定基础。 在古代,有风雷塔作伴衬,背定不是等闲之辈,与王佑郁郁寡欢的不得志的景况是一个鲜明的对照,因此,作为一个研究组织,更有弄清事实真相的职责,相当有必要分清王祜和王佑的内在关系。(作者:王天明)

王旦当国唱王“大雅”——“王祐与三槐堂
引 子
没有王旦(957年~1017年),王祐手植三棵槐树,也许只能落得个植就植了。王旦,北宋名相,王祐之子,坐实了其父“吾后世子孙必有为三公者”的预言。
在名气上,王旦似乎还不胜寇准、范仲淹等北宋名相;功业上,寇准、范仲淹等北宋名相恐怕要“稍逊风骚”。不信,那就看看范仲淹对王旦的评价——
“王文正公旦为相二十年,人莫见其爱恶之迹,天下谓之大雅。寇莱公(寇准)澶渊之役,而能左右天子,不动如山,天下谓之大忠。枢密使扶风马公知节慷慨立朝,有犯无隐,天下谓之至直。”
啥是“大雅”?
《毛诗大序》曰:“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所由废兴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
要是“大雅”还归于范仲淹的个人观点的话,谥号“文正”则是朝野上下的盖棺定论。
“文正”意味着啥?
宋仁宗的老师夏竦也很厉害,拟谥“文正”,就曾激起朝野“共愤”。
“谥之至美,文正也!”司马光当即站出来反对:“道德博闻曰文,靖共其位曰正。而夏竦奢侈无度,聚敛无厌,内则不能制义于闺门,外则不能立效于边鄙,言不符行,貌不应心。语其道德,则贪淫矣;语其正直,则回邪矣,此皆天下所共识,夏竦得‘文正’之号,不知以何谥待天下之正人良士?”
仁宗没办法,只好谥夏竦“文庄”。
自赵宋立国到夏竦(985年~1051年)去世,近百年间,只有李 、王旦、王曾,得到过“文正”之谥;之后,赵宋一代,也只有范仲淹、司马光等得到过“文正”之谥。
有宋300多年,得“文正”之谥者,不过八九人;上下40年,才能“文正”一回。
生拜宰相,死谥文正,是士大夫的“春秋大梦”。
有宋300多年,久居宰相之位、死有“文正”之谥者,只王旦一人耳,缔造浑厚朴实风。
范仲淹、司马光死谥文正,苏轼死谥文忠到了南宋而被追谥文正,多少都含有那么一点儿惋惜的味道。
惋惜他们未能长居庙堂之高,忧君忧民;希望高扬他们的精神,治国安邦。
王旦主政18年,死在宰相之位,竟然得到了文正之谥,这在文人敢于“胡说八道”的有宋一代,无论怎么说,都是一个奇迹。
真宗的宰相王旦到了仁宗一朝,甚至“全德元老”起来。仁宗立碑,亲笔为其御书“全德元老之碑”碑额。
要知道,仁宗一朝,可是个“千年名士出一朝”的时代呀:范仲淹、韩琦、富弼、文彦博、曾公亮、欧阳修、包拯、狄青、司马光、王安石、王素、宋痒、宋祁、蔡襄……
要知道,仁宗手下的这帮文人,嘴都很“赖”很“臭”,很是“缺德”的。
仁宗要给老师夏竦谥个“文正”,司马光嘴都“臭”得很;欧阳修比司马光更“别扭”,横看竖看谁都不顺眼,堪称“第一搅屎棍”。
而他,欧阳修却为王旦当起了“吹鼓手”,写起了《太尉文正王公神道碑铭》——
至和二年(1055年)七月乙未,枢密直学士、右谏议大夫王素奏事殿中,已而泣且言曰:“臣之先臣旦,相真宗皇帝十有八年,今臣素又得戴罪侍从之臣。唯是先臣之训,其遗业余烈,臣实无似,不能显大,而墓碑至今无辞以刻。唯陛下哀怜,不忘先帝之臣,以假宠于王氏,而勖(勉励)其子孙。”天子曰:“呜呼!唯汝父旦,事我文考真宗,协德一心,克终厥位,有始有卒,其可谓全德元老矣。汝素,以是刻于碑。”
素拜稽首出。明日,有诏史馆修撰欧阳修,曰:“王旦墓碑未立,汝可以铭。”臣修谨按:
……(王旦)皇曾祖讳言,滑州黎阳令,追封许国公。皇祖讳彻,左拾遗,追封鲁国公。皇考讳祐,尚书兵部侍郎,追封晋国公。皆累赠太师、尚书令兼中书令(这下,王旦祖上三代,都位列三公了)。
……(王祐)以百口明符彦卿无罪,故世多称王氏有阴德。公(王旦)之皇考,亦自植三槐于庭,曰:“吾之后世,必有为三公者,此其所以志也。”
……公为人严重,能任大事……公与人寡言笑,其语虽简,而能以理屈人,默然终日,莫能窥其际。及奏事上前,群臣异同,公徐一言以定。
……以天禧元年九月癸酉薨于家,享年六十有一。
……即以其年十一月庚申,葬公于开封府开封县新里乡大边村。
臣修曰:景德、祥符之际盛矣。观公之所以相,而先帝之所以用公者,可谓至哉!
…… ……
王旦,相真宗18年,得谥号文正而为“谥之至美”,范仲淹称其为“大雅”,仁宗赞其为“全德元老”。
王旦,何以享此不世盛誉?
王旦当国,究竟当出了个什么新的景象?
南宋学者吕中回望赵宋之世兴衰潜替,礼赞王旦当国,堪称震古烁今——
“尝究观国朝自天禧(真宗年号)以前,一夔一契之谣未兴也(夔、契都是舜时贤臣,这里当指大臣之间相互吹嘘),大范小范(范仲淹、范纯仁)之名未出也,四贤一不肖之诗(庆历新政失败后,蔡襄作《四贤一不肖诗》,谓范仲淹、余靖、尹洙、欧阳修为四贤,高若讷为一不肖)未作也,君子小人之党未分也,而张咏、孔道辅、马知节之徒,自足以养成天下之气节。胡海陵(胡瑗)之学未兴也,穆尹(穆修、尹洙)之古文未出也,三苏父子之文章未盛也,二程兄弟之学业未著也,而杨亿、王元之之文,自足以润色国家之制度。盖自李文靖(李沆,真宗时宰相,谥文靖)、王文正(王旦)当国,抑浮华而尚质实,奖恬退而黜奔竞,是以同列有向敏中之清谨,政府有王曾(王旦之后的一代名相,亦谥文正)之重厚,台谏有鲁宗道之质直,相与养成浑厚朴实之风,以为天圣、景祐(仁宗年号)不尽之用。虽缙绅之议论,台谏之风采,道学之术,科举之文,非若庆历以来炳炳可观,而纪纲法度皆整然不紊,兵不骄,财不匮,官不冗,士不浮,虽庆历(仁宗年号)之盛,亦有所不及也。”
粉碎千年封禅事
王旦,几近完美。
完美的王旦,缘何死后38年“墓碑至今无辞以刻”,以致他的孙子王素泣请仁宗“盖棺定论”?
真宗一朝,“虽庆历(仁宗年号)之盛,亦有所不及也”;真宗一朝,亦有一洗刷不掉的“污点”。
“污点”,就是装神弄鬼的“天书运动”、泰山封禅呗。
王钦若借澶渊之盟说事儿,将其愣说成城下之盟,撺掇真宗假造祥符,夸示中外,以消除真宗心中块垒:“契丹既受盟,寇准以为功,有自得之色,真宗亦自得也。王钦若忌准,欲倾之,从容言曰:‘此《春秋》城下之盟也,诸侯犹耻之,而陛下以为功,臣窃不取。’帝愀然曰:‘为之奈何?’钦若度帝厌兵,即谬曰:‘陛下以兵取幽燕,乃可涤耻。’帝曰:‘河朔生灵始免兵革,朕安能为此?可思其次。’钦若曰:‘唯有封禅泰山,可以镇服四海,夸示外国。然自古封禅,当得天瑞稀世绝伦之事,然后可尔。’既而又曰:‘天瑞安可必得?前代盖有以人力为之者,唯人主深信而崇之,以明示天下,则与天瑞无异也。’帝思久之,乃可,而心惮旦(惧怕王旦),曰:‘王旦得无不可乎?’钦若曰:‘臣得以圣意喻之,宜无不可’……帝由此意决,遂召旦饮,欢甚,赐以尊酒,曰:‘此酒极佳,归与妻孥共之。’既归发之(打开),皆珠(珍珠)也。由是凡天书、封禅等事,旦不复异议。”
真宗自称送给王旦一坛子美酒,结果竟然送的是一坛子珍珠宝物。
为办成一件事儿,皇帝竟然“行贿”臣下。
到了这个份上,倘若王旦再不屈从,王旦会是包拯、会是寇准,却再也不可能是成就“景德、祥符之际盛矣”的王旦了。
由是,“旦为天书使,每有大礼,辄奉天书以行,恒悒悒(愁闷)不乐”,他如此这般地在王朝最为盛大的典礼上,“软操”着、消解着、埋葬着天书、封禅。
他的临终遗言,更是埋葬天书、封禅的战斗檄文。
“旦遗令削发披缁以敛。盖悔其不谏天书之失也。诸子欲奉遗命,杨亿以为不可。乃止。”
****宰相,剃光头发、穿上僧衣下葬,自然是无以复加的自我惩罚。
甚至是在与当朝天子“划清你我”。
尽管“乃止”,但王旦遗言已经彻底粉碎了秦始皇以降的天书、封禅事。
自此,再也没有哪个皇帝胆敢天书、封禅了。
王旦宅第,“所居至陋,上欲为之治,旦以先人旧庐,恳辞而止”;王旦墓葬,不立碑、不搞石人石马,“棺柩暂厝于开封县新里乡大边村”。
一埋就是38年,岂是“暂厝(待葬或浅埋以待改葬)”?只是实施彻底薄葬,抑或践行其“削发披缁”的借口罢了。
38年后,仁宗以礼为王旦建造了墓园。
王旦墓在今日开封东郊边村之东,在已经宣布破产的开封联合收割机厂西墙之内中部,墓已淤没。
20世纪50年代,这儿尚有石人、石马、石羊、石方柱等裸露于地面之上,俗称“马石园”(边村又名边岗,是个高地,“马石园”没有被黄河泥沙淤积在地下)。
一位外国人,为我们留下了王旦墓老照片。
为给开封联合收割机厂让路,石马、石羊等在1958年被移到开封铁塔公园。
而今,它们还在为铁塔“站岗放哨”……
(记者于茂世)


最新推荐

江西王家大祠堂:规模
祠堂,很多人都知道,在南方是很常见的,它主要用于祭祀祖先 [详细内容]
- · 江西王家大祠堂:规模之大在全国极为罕见,
- · 他是湖北“王姓”最长寿的开国将军,打仗不
- ·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的开创者王永志院士逝世,
- · 恭祝全世界王氏宗亲网友端午节安康
- · 金门第十一届世界王氏恳亲联谊大会散记
- · 浙江百姓家谱研究会考察梅溪状元故里
- · 太子晋·王子乔与中华王氏始祖寻根
- · 余王共脉:一段坚守与回归的传奇
- · 贺泰国海南王氏宗亲会四十五周年庆典
- · 新城王氏溯源·“诸城之初家庄”确有其村







